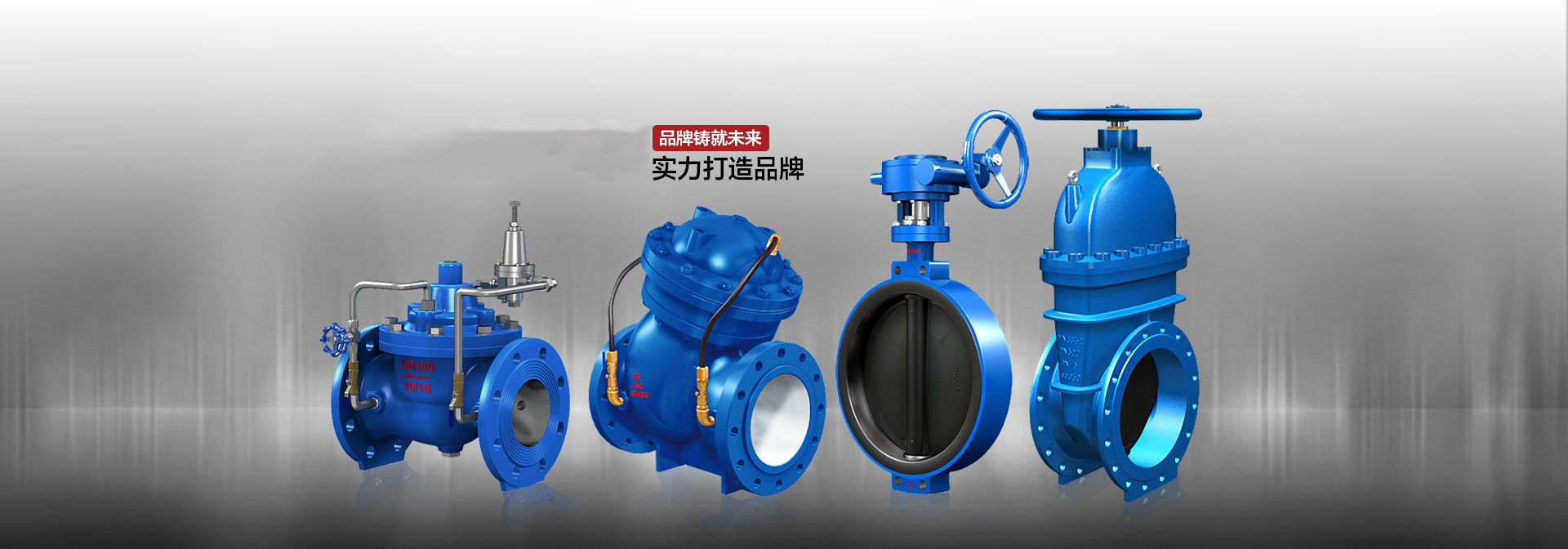本文为第一性原理系列文章的第12篇文章,关注我,可以阅读更多老头的观点。
该系列文章专注于从逻辑和第一性原理出发,分析网络中某些借用第一性原理的名义进行忽悠的观点。欢迎阅读文章的朋友批评指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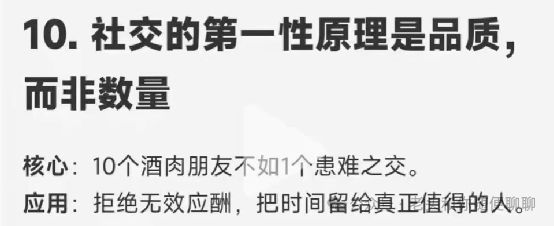
社交全称是社会交往,指个体之间相互往来、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。通过社交,人们可以结交新朋友、拓展人脉、学习新知识和技能,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和情商。此外,社交还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、减轻孤独感和增强自信心。
以上是广义的社交概念。现代社会的社交范围已经不限于现实中人与人的互动,也包括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人际互动。
笔者首先试图理解一下图片中的观点(简称“该观点”):社交的最根本目的是品质(是对方的人品?还是社交结果的价值?),其想表达的核心观念是患难之交比酒肉朋友更重要(患难之交更深层的核心因素是社交的结果—有价值),关于具体应用的建议是,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(“值得”是一个主观判断,笔者的理解是对自己有价值的人,希望没理解错)。
通过以下理解,似乎我们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人:他的所有社交活动都带着强烈的目的——现在或未来能够给自己带来某种价值(价值是什么,还需要进一步分析,情感?物质?)。
但是,每个人都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:你愿意和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人从陌生到熟悉吗?
社交品质:如何定义社交品质,是笔者理解的社交产生的结果的质量,还是其他因素,比如对方的人品。另外关于社交结果的价值,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利益抑或是其他成分,还需要继续分解分析。
无效应酬:什么样的社交属于无效应酬,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基于不同目的的社交,对此都会有不同的定义。
把酒肉朋友和患难之交两类人进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。这两类人在现实中存在着交集。
把无效应酬与值得的人也做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。这不符合现实中的实际情况。
从社交的定义来看,社交的最终核心要素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的要素包括:
该观点把社交的核心观念表达为“患难之交”(汉语的意思是在患难中结成的朋友),将其作为社交的最重要因素,忽略了社交的其他功能性需求。打个比方,如果认为“汽车的第一性原理是乘坐舒适度,而非安全性能”肯定不对——这是对社交本质的片面强调。
逻辑学角度,“品质”与“数量”二者不是同一属种的概念,不能进行对比,更不能进行二元对立。这种对立存在虚假两难这种逻辑谬误的嫌疑。
弱关系理论:格兰诺维特在描述“弱关系的力量”时,假设是,“弱关系促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”。简单说,“弱关系”最有可能向好友提供一些他们原本难以获取的信息。因此有人说,职场中80%的机会来自泛泛之交(数量),而非亲密朋友(品质)。这种说法是否可靠,可能与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现实有密切关系,比如在人情社会中,弱关系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小,而血缘、利益甚至性的关系,会更重要(网络社交平台对此可能存在影响)。
生态学类比:热带雨林的复杂生态系统,稳定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(数量),而不是仅依靠少数优势物种(品质);同样,一个社会生态的稳定性依赖的是社会的多元化,而不是少数几种关键因素。
领英(LinkedIn)有数据显示,人脉规模扩大与职业机会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,与关系深度无显著相关(需要提醒:这个数据可能与当前社会现实存在差异)。
不同的人、人生的不同阶段,对社交的要求是不同的。该观点有仅仅从单一静态视角进行片面总结的嫌疑(以偏概全)。以职业发展为例:
职业早期:通常需要通过广泛社交(数量)积累行业认知、寻找更多的合作者或指导者;
比如,初期创业者,往往需要通过大量参加各种活动来接触潜在的客户、合作者、投资者(数量)等,后期再筛选核心伙伴(品质)。初期如果一味地拒绝“无效应酬”,很可能错失机会。
对“有效”和“无效”的主观价值判断,易忽略隐性价值。很多时候,有些看似无效的社交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创造价值:
积累信任:长期的互动,是陌生人之间积累信任的基础之一,有了信任,才有可能获得对方在特定场景下的背书;
汉语中酒肉朋友是一个贬义词,指那些在一起只是吃喝玩乐而不干正经事的朋友;从现实角度,“酒肉朋友”与可能的合作伙伴没有绝对的分野(反例:仗义每多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)。
从情感视角,患难之交也有可能因三观分歧走向决裂。比如,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,太多的创业团队因为种种原因而散伙。
传统文化中,社会中所谓的“人情关系”,不乏这样的情形:核心要求仅仅是维持表面的关系,而不是共同做事,甚至有可能反目成仇或背后捅刀。
或许,该观点来自于邓巴数字(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,罗宾·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理论):人类社交网络的节点不会超过150个,即和你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在150人以内。有人根据邓巴理论总结:在繁杂的社交网络中,真正能够带来幸福和快乐感的,永远只取决于三十人左右的亲人好友圈。
邓巴数字似乎并不能为该观点提供有效证据(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这个理论并分析,简单说,邓巴数字的核心是幸福和快乐感这一主观感受而非广义的社交)。
从生物学(物种与生态)的角度来看,物种的生存依赖于种群规模、物种多样性(数量)与该物种的生存能力(质量)之间的平衡。同样,社交活动的最终价值,比如一个企业的产品,也不能完全依赖少量关键因素。新产品、新技术的普及需要一定的用户基数(数量),如果仅靠少数“高粘性用户”,市场规模必定受到限制(细分市场不代表不需要一定的规模)。
社交本质并不能简单表达为人品(人品通常是一个基于道德观的主观判断)或有无价值,因为这个因素还能够继续分解,比如感情、信息、资源、风险等等;规模效应与弱关系理论对于社交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;价值不能单纯依赖主观判断,最不能低估的是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对社交规则的影响。
从社交活动中获得情感支持和物质性帮助,无可厚非;注重社交的价值,精准地选择和维护有价值的关系,从而提高社交效率,同样符合人性的要求。例如,与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,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,能够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,提升生活的幸福感。
同时,也要认识到,不同的社交场景,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。比如,商业社交,广泛的人际关系可能提供更多机会;个人情感支持方面,深度关系更为关键。另外,社交关系是动态变化的,过度关注价值,这个目的过于功利。
特别重要的一点,由于评价标准的主观性,不同的人对“真正值得的人”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,可能忽略社交的复杂性,比如情感、利益、环境等,导致对不同观点和文化的接触机会减少,不利于全面发展。
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可以拓宽视野,激发创新思维。例如,结识不同行业的人可能会带来新的灵感和合作机会,而局限于少数深度关系中可能会限制这种可能性(这完全基于个人选择,没有统一标准)。
社交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简单粗暴地表达为价值依赖,是对第一性原理的错误应用,有可能带来可怕的负面影响。
如果不能说明具体的适用场景和适用人群,这种表达真的涉嫌忽悠;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交活动都是如此,很可能会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(特别是陌生人之间)产生严重破坏。